 安徽省重點新聞門戶網站
安徽省重點新聞門戶網站
 安徽青年報官方網站
安徽青年報官方網站
在合肥,他們幫助560個走失的人回家
一個尋常的早晨。
你出門前,母親還坐在熟悉的沙發(fā)上看電視,背影安穩(wěn)。
你叮囑了一句“媽,我走了”。
她或許含糊地應了一聲,或許沒有。
這與你生命里成千上萬個出門的早晨,沒什么不同。
但當你再次推開門,屋里一片寂靜。
“媽——”無人應答。
房間里,街道上,所有她可能去的地方,都沒有她的身影。
那一刻,世界突然失去聲音。你不知道她去了哪個方向,是否寒冷害怕,甚至不知該從何找起。
在合肥,有一群人每天都在對抗這種“消失”。
2016年至今,合肥市藍天救援隊“勿忘我”防走失項目組已經幫助了560余人回家。
他們?yōu)閯e人的父母、兒女,拼命找回那個轉身之前的世界。
55歲,他說:“只要我還有體力,我會一直參與”
推開那扇門的一刻,倪文華看見一個穿著紅外套的身影,蜷坐在6樓的角落里。
時間已經是凌晨1點多。
他怔住了,一股強烈的感覺攥住了他。
這是55歲的倪文華第一次找到走失者的記憶。
一位90多歲的老人走失在雨夜里,監(jiān)控范圍最后鎖定在一個小區(qū)。
他和隊友負責一棟樓的搜尋工作,從32層開始,一層層向下尋找。
“如果當時沒有找到......”倪文華沒有說下去。
他后來參與了太多野外搜尋,深知“找到”與“沒找到”之間,有時隔著的就是生與死。
“我們尋人,要不走尋常路。就往那些樹林的里面,越難走越要鉆。”
走失者,尤其是精神恍惚或有意回避的人群,往往本能地避開開闊和顯眼的地方。
“有時候在野外找到一個走失者,相當于拯救了一個生命,讓一個家庭變得完整。”
倪文華的手背上布滿細密的、已經結痂的劃痕,像一張暗紅色的地圖。
那是灌木叢的荊棘留下的,衣服被劃破是常事,手也腫過。
“這都很正常,”他語氣輕松得像在說別人的事,“這些都是小的刮傷。”
問他最大的困難是什么,他沒有提體力,也沒有提危險。
“未知性。每一次出發(fā),結果都是未知的。”他說。
付出時間、體力、全部的心力,卻不知道路的盡頭是溫暖的團圓,還是冰冷的遺憾。
這種懸而未決的沉重,遠比身體的疲憊更難承受。
“一旦有好的結果,心里的那種欣慰,超乎尋常。”
年齡在他這里,似乎只是數字。
“我還能做,就想做點什么,盡自己的一份力量。”倪文華說:“我會一直參與下去,只要我還有體力。”
她說:“無論生死,我都要帶他回家”
43歲的張宣是尋人隊伍里少有的女性。
她不害怕直面死亡,也不避諱談論它。
張宣參與的第一次尋人任務,就是尋找一位患有阿爾茨海默癥的老人。
老人從家中走出,一路跨越快車道的欄桿,沿著一條白色的堤壩一直走,最后消失在了河水里。
那個清晰的軌跡和殘酷的終點,給她上了沉重的一課。
“生與死,都要帶他回家。”這是張宣參與尋人的初衷。
比起明確的死亡,那種憑空“消失”帶來的懸空感,是家庭永久的缺口,每到團圓時刻便隱隱作痛。
張宣認為,尋人最重要的是要有耐心。
在隊伍里,她尤為擅長“追監(jiān)控”。
追監(jiān)控是技術與耐力的雙重磨礪。時間被切割成以幀為單位的碎片,在無數個路口、街角,反復倒帶、播放、定格。
任何一個細節(jié)的誤判,都可能讓整個搜尋推倒重來。
有一次,為了追查肥西一位走失老人的身影,她從晚上7點一直盯到了早上10點。
腰背已經僵硬。但她心里是踏實的,甚至有些“慶幸”。
“監(jiān)控在動,我就踏實。有軌跡就有希望。”
更多的時候,走失發(fā)生在監(jiān)控之外,比如郊野、荒山、密林。
一次進山搜尋,她和隊友在植被瘋長的山林里跋涉了三個多小時,刀用來開路,割開擋路的荊棘。
樹密,刺多,回家后她發(fā)現隊服和里面的棉毛褲上扎滿了細小的植物倒刺。
一雙質量頗好的作訓鞋,鞋跟竟生生走斷了。
尋人的電話常在夜晚響起。起初家人不理解:為何深更半夜貼錢貼時間,去找陌生人?
張宣沒有爭辯,只是一次次地和他們分享那些失而復得的故事。
現在,她半夜出門時會留張紙條:“我去尋人了,不用擔心。”
愛人知道,電話響起,就是有人需要他的妻子帶他們回家。
他說:“別人幫助了我,我也想去幫助別人。”
救援結束后,常有家屬小心地問:“費用大概多少?”
“不要錢。”他們總是溫和而堅定,“我們是志愿者。”
無償的善意,比明碼標價的幫助更讓人震動。
而在這些被震動的人群中,有人選擇用更長的方式去回應這份善意。他們轉身加入了這支隊伍,從被幫助者,變成了幫助者。
汪春生就是其中一個。
2024年冬天,汪春生的舅舅走失了。
在合肥市藍天救援隊的幫助下,最終找到了人——遺憾的是,生命已經離去。
那是一種混雜著感激與巨大悲痛的復雜感受,感激于有人全力以赴,幫他們找到了親人,給了家庭一個確切的答案;悲痛于這個答案本身,是如此殘酷。
“別人幫助了我,我也想去幫助別人。”汪春生說。
這樣的善意循環(huán),在這些志愿者中默默傳遞。他們沒有豪言壯語,只有一些非常樸素的希望。
干洗店老板王柱是尋人隊伍中出勤率最高的隊員之一。“有任務的時候,我有能力有時間,就盡可能去。”
一次,他和隊友只用4個多小時,就幫助一位走失的老人回家。“只有親身體會,才知道家人分離的焦灼。”
余濤是一名無人機飛手。有些人力不太容易進入的區(qū)域,可以用無人機快速排查。
“在尋人的過程當中,時間是非常寶貴的。有很多老人可能走失一晚,就會發(fā)生意外。”這也是他參與尋人的初衷。
“夏天,在飛的過程當中,蟲在身上咬,又癢,但又不能去拍。”余濤說。
冬天,則是另一種考驗。一個架次通常飛行約三十分鐘。在寒風中,操控者需要保持手指的穩(wěn)定與敏銳,去推拉操縱桿,雙眼更要一眨不眨地追蹤屏幕。
“等到飛完,全身都凍僵了。”
這些忍耐,在發(fā)現走失者的那一刻,全都化為巨大的驚喜。
一次,他們通過紅外鏡頭在第一架次就迅速定位到一位走失老人。“老人當時已經受傷了,幾乎沒有了行動能力。”
無人機在老人上空懸停。通過對講機,地面隊友被引導至精確位置,將老人平安背回。
最漫長的一次飛行,他和隊友從凌晨一兩點,操控無人機飛行至第二天上午十點。
無人機以他們?yōu)閳A心,在上空織就一張密密麻麻的“蜘蛛網”軌跡。
他們說:“我們要找到那個人”
在合肥市藍天救援隊“勿忘我”項目組負責人羅浩的腦子里,常年運轉著一套精密而復雜的算法。
輸入的是零碎的線索、模糊的監(jiān)控片段、家屬焦慮且可能有所保留的敘述,以及合肥周邊錯綜復雜的地形圖。
他需要輸出的,是一個盡可能精確的搜尋方案。
“東西南北你得能分清楚,地形地貌你得心里有數。”這是基本功。
但更難的,是與人的溝通。“怎么讓家屬說出一些他不愿意說的事情?”
羅浩說,走失背后常有隱情,或許是家庭矛盾,或許是個人心結。
家屬出于隱私或愧疚,可能下意識地掩蓋關鍵信息。
他因此練就了一種近乎偵探的敏銳與耐心,需要從閃爍的言辭、情緒的起伏中,“抽絲剝繭”地還原出走失者出走前的真實狀態(tài)與潛在路徑。
“就像分析一個案件一樣,一層一層找到線索。”
他記得一個冬天的尋人任務,線索一度中斷,但他仿佛被一股執(zhí)念攫住,“每時每刻都會在想著他到底會按照什么樣的路徑去走”。
他讓自己徹底“成為”那個人,沿著監(jiān)控里最后出現的路,一步步走下去。
走到一個岔路口,強烈的直覺告訴他:“他不應該再往前了,應該就在附近。”
搜尋力量向那片區(qū)域集中,最后人在那里被找到。
羅浩說,許多隊員和他一樣,“魔怔了”。
“有時候我們坐著倒杯水休息,腦子里全是各種可能性:他會怎么走?往哪走?但凡有一絲可能性,我們都會再去看看。”
這種狀態(tài),源于一個共同信念:“必須找到。”
它不浪漫,甚至有些殘酷,但卻是對生命最大的尊重,是對“消失”最決絕的抵抗。
“勿忘我”
“勿忘我”這個名字,誕生于對抗遺忘。
合肥市藍天救援隊隊長蘇琴說,尋人任務幫助的大多是阿爾茨海默癥患者。
“他們甚至忘了自己是誰,忘了子女的名字。雖然他們忘了,但那種愛還在心里。”
去年臘月里,深夜11點她接到求助:一位70多歲的老人中午走失,全家人找了一下午沒找到。
那個晚上,20多名志愿者從家中趕到現場,路搜、調監(jiān)控、無人機熱成像搜索分工展開。
凌晨1點多,在零下1度的氣溫里,老人終于被找到了。
她的兒子趕來,一把抱住母親哭出來:“老娘你跑哪去了!”
那晚,在場所有人在凌晨的街頭拍下一張合影,“每個人都笑得特別甜,我們被那種失而復得的喜悅感染了。”
救援隊的求助電話常在深夜響起——那往往是一個家庭已用盡所有辦法,依然尋無所獲的時刻。
“我們一出動,常常就要找到凌晨兩三點,有時甚至到天亮。”蘇琴說。冬夜的寒風、夏日的蚊蟲、漫長的監(jiān)控、泥濘的山路,對他們而言已是尋常。
“辛苦,但值得。我們能配合公安、陪著家屬,做一點真正有意義的事。”
“城市是需要溫度的。”蘇琴說,在這座千萬人口的城市里,他們這群志愿者守護著一種最樸素的信念:不讓任何一個轉身,成為永別。
(記者 呂文衛(wèi))
- 2025-12-09 靈璧縣少年科學院組織開展第四十三課科普課堂系列活動
- 2025-12-09 靈城鎮(zhèn)團委開展“暖冬志愿行,情滿靈城鎮(zhèn)”主題志愿服務活動
- 2025-12-09 靈璧縣2025年“青馬工程”暨團干部和少先隊工作者能力素質提升班圓滿結束
- 2025-12-09 團靈璧縣委:薪火少年解鎖非遺第十課·手繪鐘馗
- 2025-12-09 淮南市大中小學誦讀紅色詩詞思政大課在淮南師范學院舉辦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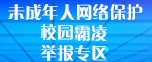
 贊一個
贊一個
